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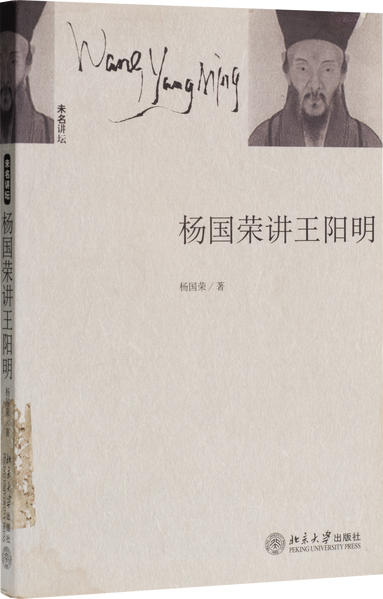
书籍信息
作者:杨国荣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9月
ISBN:9787301092385
推荐理由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介绍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普及读物。王阳明心学在我国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从史论结合的角度辨析、阐述了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思想发展、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影响。该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具有较好的可读性,适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杨国荣,1957年10月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8-2000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澳大利亚跨文化研究杂志Inter-Cultural Studies顾问。1994-1995、1999-2000以及2002年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作学术研究。
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讲 心学形成的历史前提
一、性即理及其他:形上本体的强化
二、心与理的紧张
三、徘徊于朱陆之间
第二讲 心体的重建
一、心体与性体
二、心即理
三、成圣的内在根据
第三讲 心与物
一、心物之辨的内在涵义
二、存在与境界
第四讲 德性语境中的良知
一、德性的涵养
二、德性与道德行为
三、德性与规范
第五讲 群己之辨
一、成就自我
二、人我之间
三、无我说
第六讲 致良知
一、良知与致良知
二、本体与工夫
第七讲 知行之辨
一、知行之序
二、知行关系的展开
三、知行合一与销行入知
第八讲 心学中的名言问题
一、心体与言说
二、名言与道
三、“说”与“在”
第九讲 心学与晚明思想
一、泰州学派
二、童心说与个体原则
三、性体的回归
四、致良知说的展开
五、东林学派与心学
第十讲 明清之际的心学
一、工夫所至即是本体
二、个体与整体之辨
第十一讲 心学的近代回响
一、良知与个性
二、良知与直觉
三、心力与意欲
四、知行合一与性修不二
后 记
试读
引 言(节 选)
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尽管他们的思想每每以“极高明”为指向,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斋生活。
康德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一例。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诚然在哲学上进行了一场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但终其一生,却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生活其间的小城。他的时钟般的刻板生活,似乎构成了近代学院哲学家的经典范式。
相对于这一类的学院哲学家,王阳明的一生显得颇不平凡。作为哲学家,他固然有过龙场悟道之类的哲学沉思,但这种沉思并非完成于宁静安逸的书斋,而更多地是以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等人生磨难为背景。
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到晚岁的哲学总结,王阳明的哲学历程与其曲折的人生旅程处处融合在一起,为学、为道与为人则相应地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王阳明早年便已对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问题发生兴趣,12岁那一年,他曾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以为,第一等事无非是科举及第,王阳明对塾师的这种回答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真正的第一等事,应当是“读书学圣贤”。
所谓学圣贤,意味着以内圣之境为目标。随着其思想的逐渐成熟,成圣作为“第一等事”也越来越成为王阳明自觉的追求。正是围绕如何成圣这一问题,王阳明作了长期的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结果,即具体体现于王阳明的语录、论学书札等等之中。
王阳明的一些门人后来将集中反映其论学宗旨的语录、书信等汇编起来,《传习录》便由此而形成。
《传习录》三卷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王阳明心学的全貌。从时间上看,它收录的是王阳明思想成熟期的论述,就内容而言,它几乎涵盖了王阳明心学的各个方面:从心性之辨到心物关系,从致良知到本体与功夫,从知行合一到万物一体,都纳入了《传习录》的论题,而王阳明心学的主要论旨、思想倾向,也可以通过《传习录》而见其大概。
从某种意义上看,《传习录》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主要载体。
正如康德试图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解决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样,理学将心性的辨析视为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当然,以心性之域为入手处,并不意味着由此展开的仅仅是单一的哲学路向。
事实上,首先正是在心性之域,程朱一系的正统理学与心学表现出不同的立场。程朱以性为体,性又与理合而为一;与性体的建构相应的则是以性说性,化心为性;由此建立的是一套以性体为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
与性体至上的形而上学系统相对,陆九渊将心提到突出地位,并以此为第一原理。不过,陆九渊对心体的理解本身具有二重倾向,而其中的个体性规定则在陆的后学中逐渐开始向唯我论衍化。个体意义上的心与形而上之性的对峙,表现了理学的内在紧张。
在化解心性之辨的如上紧张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的是王阳明。以心体的重建为逻辑前提,王阳明力图在心学的基础上化解形而上与形而下、个体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存在与本质、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主体间、本体与工夫等紧张,从不同的层面对内圣之境何以可能作出理论上的阐释;在心学的逻辑展开中,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等呈现为统一的系统。
相对于程朱一系的正统理学,心学之思无疑表现出哲学视域的多方面转换;从更广的意义上看,心学又构成了中国哲学历史演进的重要一环
当然,作为历史中的体系,心学本身又蕴含着内在的张力。如心即理、致良知这些基本命题所表明的那样,心学的思考一开始便呈现出二重品格:心体所内含的个体性规定及存在之维与理所表征的普遍性规定及本质之维、先天本体(良知)与后天的工夫,等等,这些关系应当如何定位,始终是一个理论的难题。
在晚年的四句教中,王阳明试图提升个体并确认其存在的多重向度,但又难以放弃普遍本质对人的预设;试图扬弃本体的超验向度,但又无法拒斥对本体先天性的承诺。这种理论上的张力,亦表现了心学在哲学上的转换特征,而从心学本身的历史演进看,以二重性为表现形式的内在紧张,又进一步引发了王门后学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