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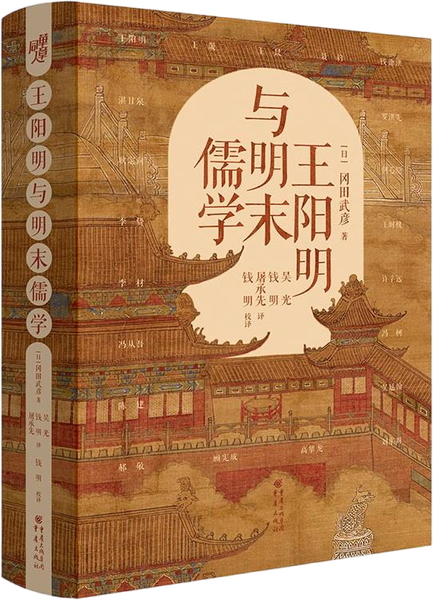
基本信息
(日)冈田武彦 著;吴光,钱明,屠承先 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5-01
ISBN:9787229163204
书籍介绍
本书是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的终身代表作,也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为背景,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产生原因、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以及分化演变后各家各派学术宗旨的异同,并将王门学派与明代尤其是明末其他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哲学家的思想,将个性化的理解和思考融入叙述中,作品既充满古人之义理,又饱含自己之哲思。其叙述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行云流水且汪洋恣肆;其用词是典雅的,也是简练的,毫无赘语而直入核心。
作者介绍
冈田武彦(1909—2004)生于日本国兵库县姬路市。1934年毕业于九州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授,196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退休,后任九州大学名誉教授。2004年病逝于福冈市。主要著作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中国与中国人》《现代的阳明学》《儒教精神与现代》《王阳明大传》等。此外还有《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著,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明代的文化与思想
明代精神文化的嬗
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分化
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论
二 明学的源流
全体大用的思想
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展开
元朝的儒者
明初的大儒
朱陆同异论的源流
从吴澄到程敏政的朱陆同异论
第二章 王阳明与湛甘泉
一 总论
二 王阳明
阳明心学的先驱
以科举为目的的书院教学
自鹿洞书院的学规
“学三变”与“教三变”
“知行合一”说
“事上磨炼”说
为学之头脑
“致良知”说
“格物”论
“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
本体工夫论
“万物一体”论
三 湛甘泉
以天理为学之头脑
浑一之学
心性合于一
工夫即本体
中正即道
知行并进
随处体认天理
全放下
以自然为宗与“两勿”论
“格物”论
第三章 王门三派
一 总论
二 现成派(左派)
直下悟入
“四无说”与“四有说”
“无中生有”说
“生几”说
浑然即一
“范围三教”
王艮的思想
三 归寂派(右派)
“归寂”说
“研几”说
“虚寂”之体
“致中”与“致和”
“夜气”之存养
“戒惧”与“思”
“格物”说
“万物一体”说
四 修证派(正统派)
知觉即性
真诚恻怛
“慎独”与“戒惧”
主工夫而言本体
循其良知
实地用功
第四章 现成派系统
一 总论
平实派
容禅派
气节派
旷达任诞派
现成派之展开
二 罗汝芳
从无入有
“悟”与“信”
赤子之心
“孝、悌、慈”三德说
“仁”之生机
三 周汝登
当下之信
浑一之体
贵自得
悟得真己
《九谛》与《九解》
《圣学宗传》
四 耿定向
初心之生机
庸德庸行
“四句教”解
实修实事
异端之辨
五 何心隐
心隐之气节
贵“意气”
实事实用
设聚和堂
六 李贽
以实用为宗
道为虚空
童心说
晚年好《易》
附录 论《说书》
关于《说书》
关于《说书》之思想
第五章 归寂派系统
一 总论
二 王时槐
“虚寂”说
“生几”说
性命论
“透悟”说
第六章 修证派系统
一 总论
二 李材
心性之辨
摄知归止
直达性命
修身为本
止修并举
性体工夫
第七章 湛门派系统
一 总论
二 许孚远
“克己”之学
评王门现成派
先工夫后本体
三 冯从吾
异端之辨
驳“无善无恶”
“一体”之旨
第八章 批判派与复古派
一 总论
二 冯柯
圣学致用
定理实存
循礼穷理
朱王之辨
王学批判论
陆王之别
三 陈建
陈建的影响力
“心性相随”论
陆学归禅
主敬穷理
异端之辨
四 吴廷翰
理气浑一
“中”为性体
心性之辨
物实理虚
工夫次第
五 郝敬
事外无理
先行后知
性习不离
实用之道
自然之动
习而成圣
养气为要
第九章 东林学和刘宗周
一 总论
东林学之发端
刘宗周之学
二 东林学
东林学的本旨
性善说的复兴
心理一体论
反身而诚
中庸之道
主静未发
太虚思想
工夫之修
三 刘宗周
主宰即流行
性非定体
意念之别
喜怒哀乐之“中和”
好恶之意
“慎独”说
以意为体
诚即思、思即诚
初版译后记
再版校译者后记
书籍试读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中国文化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暂时性有极为深刻的体认,由此而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有深刻的多元揭示,那些揭示一直是中国文化进行深度反思与不断重建的基本主题。
相对于宇宙生命的博厚高明与悠久无疆,个体生存的有限性是作为一个经验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若蝇营狗苟而与草木同腐,则人的生命尊严尚且不存,更谈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故凡一切哲学、宗教、艺术之创设,就其本质而言,皆试图为人的存在别开生面,以开辟其存在畛域而丰沛其意义,从而实现对于暂时性的超越。
“不朽”是源发于人类生命自身的一种本原性期盼。而在中国文化中,基于个体生命之有限性与暂时性的根本体认,“不朽”的思考被转换为两个基本面相:一是现实生存过程的价值实现,被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二是经由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之存在本质的同一性确认,最终实现“内在超越”。
在儒学语境中,前者是“下学”,为工夫;后者是“上达”,为本体。作为同一个生命过程的不同侧面,“下学”即“上达”,工夫即本体。这样,现实的经验生存所展开的全部生命活动,才会因存在之本原意义的充分彰显而成为神圣人生的组成部分。
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全部学说,既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思想体系的广泛整合,更是其自身生活实践的内在领悟。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他以儒家学说为其思想构建的根基,广泛吸纳包括佛、道在内的不同思想形态以及宋代以来新儒学的思想成果,融会之以贯通;在独特的问题意识的主导下,构建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的根基是“心即理”,是关于人的存在本原同一于天道自身之实在性的明确肯定。这一基原或可被称为“极”。正因为有此“极”作为基础,阳明先生对不同思想体系的重新整合,才能“会其有极”而“归其有极”,呈现出不同视域融合下的新境界。其思想体系虽博大高明度越前人,但条理密察、秩序井然。
对于“心即理”的肯信,在个体自身是通过主观认同而内在完成的,其实质是个体对自身全部经验活动和生存方式之意义与价值指向的自我“立极”,从而促使“主体性”在个体自身的自觉建立,并因此而使普泛意义上的“个体”实现向“主体”的转变。个体的存在性既然转变为主体性本身,那么主体性的表达与存在性的彰显便全然是同一的,把这一点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便是“知行合一”。
在阳明先生那里,“知行合一”不只是一个知识论命题,也是一个存在论命题,是主体自身的存在性得以表达与实现的根本途径,既是主体的在世生存方式,也是通过世间生存而上达于天道这一最高的本原实在,并与之全然同一的生命道路。因此,切实践履“知行合一”之功,人们就不仅在开辟着自己的生活世界,并且同时在把生活世界转变为意义与价值世界。
正是在“知行合一”之下,信仰与行动实现了统一,存在与价值实现了统一,本体与工夫实现了统一,下学与上达实现了统一,此在与超越实现了统一。正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世间的生存因此被注入丰沛的意义,从而彰显了其本原性的崇高与庄严。
阳明先生亲身践履和不断体证“知行合一”说,至晚年进一步揭示“致良知”说,使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进一步臻于完密。从根本上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内涵是一致的,只不过“知”变成了“良知”。“良知”即天道之在人者,是人的本原性实在,是最高实在本身;“致”则是推致,强调的是由主体性所原发而外现的行为,在经验生活中,“致”必然涉及特定关系情境中的对象,也就是“事”(人物、事件)。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也是“极”,是天道本原的大中至正。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关涉的事物会不中不正,原因显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从事的人不能“致良知”而使其失去本然之中正。因此,阳明先生的“致良知”说,是要求人们将本有良知的大中至正实现出来,落实到与之交往的一切人物事件之中,还原事物本身,“物各付物”。天道之永恒中正的实现,是为最高善,也就是“至善”。
人心之本体,原是“天渊”,无广狭,无短长,无前后,无内外,无限量,虽本无一物,而无物不摄。“致良知”,即表达主体之本原实在性的实践活动,是把原来相对于主体为“外”的事物不断涵括于主体自身之“内”的过程,而终至于“心外无物”,最终达到无限广袤、无限阔大、无限空灵的生命境界。
不过,在阳明先生那里,“致良知”而至于“心外无物”,不过只“物各付物”而已。的确,在人类的思想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其他学说,能够像阳明先生的“致良知”说那样,更有益于人类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更有益于主体自身实践境域的开辟及其价值世界的构建了!
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三不朽”的“完人”,他的一生,是立志成为圣人而终至于圣人境界的一生,是不断践行“知行合一”“致良知”而终能亲证“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一生。
然而,他的生命途程,是艰难的、困顿的、危机四伏而波诡云谲的,而对阳明自己来说,却又是坦荡的、光明的、胸次洒落而实现了天下万物之浩然同体的。
了解阳明先生的一生,体悟其全人格的光明峻伟,感受其生命道路的波澜壮阔,领略其精神境界的无限辽远,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深刻领会其思想精髓,更能为我们的现实人生带来深邃启迪,从而有益于我们自己实践境域的开辟与价值世界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