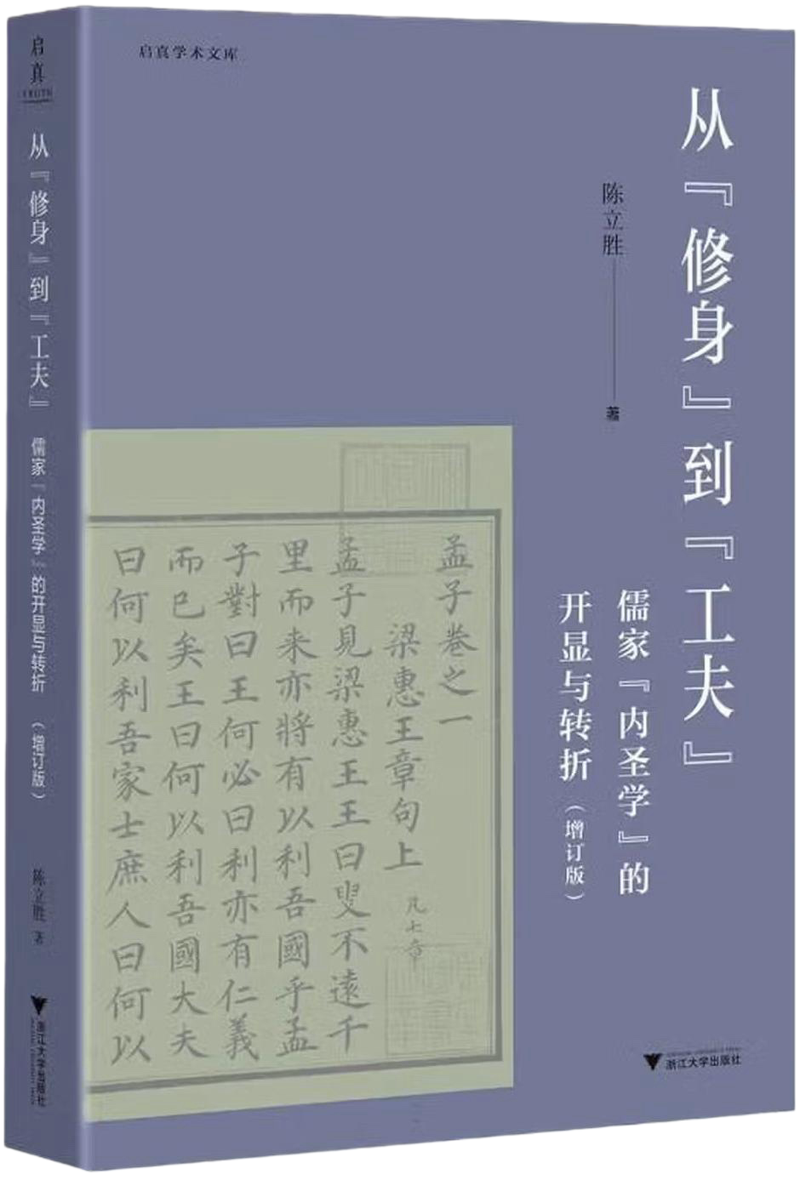
从“修身”到“工夫”: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
陈立胜
出版时间:2025-05-0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259828
书籍介绍
本书讨论的是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涵盖古代到现今儒家修身学的发展历程及其转折变化。全书深入揭示了儒学修身传统中自孔子孳乳而至宋明粲然大备的反省技术与类型,既有对治怒、“梦工夫”、静坐、慎独和立志等修身技艺清晰之呈现,更有对“朱子时刻”开启的“独知”话语之长时段、历时态的脉络之分析,堪称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儒家修身哲学史专书。
作者简介
陈立胜,山东莱阳人,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特聘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宋明理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等。
书籍目录
导论 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
一、“修身”:德行培育的时代
二、“工夫”:心灵操练的时代
三、“觉悟”:“过渡时代”
四、“设计”:人机一体时代修身会终结吗?
五、结论
第一部 儒家“内圣学”的开显:德行培育的时代
第一章 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一、轴心时代说
二、以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
三、士的“身位”
四、“修身”是中国轴心期突破的一个主题
五、“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第二章 “修己以敬”:儒家修身传统的“孔子时刻”
一、孔子之前的“敬”
二、《论语》中的“敬”
三、修己以敬:为己之学的自反性向度
四、余论
第二部 儒家“内圣学”中的反省向度与修炼技术
第三章 “慎独”、“自反”与“目光”:儒家修身学中的自我反省向度
一、“鬼神的目光”
二、“他人的目光”
三、“心目之光”
四、结论
第四章 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
一、一生生命历程的反省
二、一天行为之反省
三、对意念的反省
四、与意念同起的反省
五、结论
第五章 “治怒之道”与两种“不动心”:儒学与斯多亚学派修身学的一个比较研究
一、引言
二、儒家治怒之道的谱系
三、斯多亚的“怒”观与治怒五法
四、中西治怒之道的异同与两种“不动心”
第六章 “梦”如何成为工夫修炼的场域:以程颐说梦为中心
一、引言
二、以理照梦
三、睡时功夫
四、“梦工夫”的四种类型
五、两个结论
第七章 宋明理学中的静坐类型及其效用
一、引言
二、作为默识仁体的静坐
三、作为收敛身心的静坐
四、作为观天地生物气象的静坐
五、作为省过法的静坐
六、四种静坐的效用与关系
七、结语
第八章 宋明理学如何谈论“因果报应”?
一、引言
二、儒家德福一致问题之缘起
三、先秦儒学“德”与“福”的剥离及其问题
四、宋儒:以“感应”代“报应”
五、心学德福一致化思潮
六、儒家“修身”与“教化”的两套话语系统
第三部 儒家“内圣学”的转进:心灵操练的时代
第九章 作为工夫范畴“独知”的提出:儒家慎独传统中的“朱子时刻”
一、朱子之前的“独知”一词
二、朱子以“独知”解“慎其独”
三、朱子独知新解之“修缘”
四、朱子独知新解的工夫论背景
五、两个工夫抑或一个工夫?
六、“戒惧”与“慎独”之异同
七、“独知”新解的历史效应
第十章 从“独知”到“良知”:王阳明论慎独
一、“独知”:从朱子到阳明
二、“独知处”即是“吾心之良知处”
三、“独知处”究竟如何用功?
四、由“独知”而知“独”
五、结论
第十一章 王阳明思想中的“一念”两义说
一、作为“意念”之“一念”
二、“意念”之发与良知之“自知”
三、作为“戒惧之念”之“一念”“念念”
四、总结、引申与问题
第十二章 湛若水“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一、“岭学”与“越学”的互动
二、湛若水:由“独知”到“独体”
三、湛若水后学的“独”学与“研几”学
四、湛若水“独体”观念的历史效应
第十三章 “独”—“几”—“意”:阳明心学一系工夫演进中的三个“关键词”
一、“念起念灭”困境、对“发处”用功的质疑与“本体工夫”意识的觉醒
二、由“独知”到“独”
三、由“独”到“几”与“意”
四、结论
第十四章 “无工夫之工夫”:潘平格的登场与理学工夫论的终结
一、引言: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
二、辨清学脉:寓“立”于“破”
三、“盘桓于腔子”:破宋明理学工夫论
四、立真志:无工夫之工夫
五、潘平格工夫论的思想史定位
附录:郑性与潘平格
附录一:“工夫”一词之说明
附录二:“内圣学”一词之说明
附录三:全书架构之说明
参考文献
补记
精彩试读
一、“修身”:德行培育的时代
修身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如《书经·皋陶谟》《逸周书·书序》已有“慎厥身修”“修身观天”“修身敬戒”等说法。周公明确地将“天命”与“德”联系在一起,原本“嗜饮食”“不敬鬼神”的天、神,转而成为超越族类与世俗物质利益的“德”“惟德惟馨”“惟德是辅”的道德神。就此而言,两周政治文化已经具备了“崇德贵民”的人文主义底色,代表世俗的道德理性与政治理性的“鬼神传统”逐渐压倒了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天官传统”。与此相悖,礼乐文化之中的仪式意义逐渐内化为德性、“仪式伦理”向“德行伦理”过渡是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周人“敬德”观念,诚如徐复观指出的那样,其背后的“忧患意识”具有“道德的性格”。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现象,即周公对德行的重视其根本的目的始终未脱离“获得天命”“守慎天命”这一终极视野。“敬德”与“受命”、“德”与政权的“天命”往往联结在一起,对“德”的追求虽不乏真诚与坚定(“厥德不回”),但其动机都始终无法超越政权的“受命”这一高度(“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坚持有教无类,使得修身带有开放性,在原则上它不限定于某个阶层,后来的《荀子·君道》与《礼记·大学》都明确指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吏乃至庶人皆以修己、修身为本。孔子又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尽心下》则说:“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显然,孔子对德行的追求不仅具有了普遍性,而且也拥有纯粹性。由“受命”向“俟命”、由古老的善恶有报的宗教信念向德福剥离、由“行仁义”向“由仁义行”的转向中,德行获得了自身的纯粹性与自足性。余英时指出,春秋前半段尤其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孔子出生前一个世纪左右),“修德”已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但这个“德”仅限于诸侯、执政、卿大夫,仍未触及一般人,“德”尚未具有普遍性。另外,“德”虽已开始“内在化”,但以何种方式内在于人,亦指示未清,此中关键尚未出现“心”的观念,故这个时期只能称为轴心时代的“酝酿期”。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早期儒家的德行修养乃扎根于“礼乐文化共同体”。礼乐不只是发生在某种特殊领域的礼仪与音乐现象,还是涵盖宗教、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生各个面向的规范与仪式,是沟通天地人神、传承历代圣王德行与风范的乐舞,是政教合一的古典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儒家文明的基因。故贵族与士大夫普遍重视具有政教色彩的“威仪的身体”之展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卫国北宫文子论威仪的一段经典文字最能说明问题:“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或地区,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官家。顺是以下皆如此,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或地区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谟若之,则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藏善于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均注重在“上”者临下所呈现出的身体之威严及其可象、可则、可观的示范性。这种威仪之身是伦理政治的“具身化”。“威仪观下的贵族形象,仿佛一座威严的屏风,你只能从远方眺望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仪容并肃然起敬,却无从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种威仪之身无疑注重“动作”,但因此而断定它只是“外在的气象”而与人的理性或心性缺乏内在的联系,恐也不符合上述余英时所称的“精神向内运动”的事实。威仪之身是一种“敬畏天命”的身体姿态,不过,“如果和孔、孟以后的儒家伦理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威仪观最大的特色,乃在它是以社会共同体规范的身份展现出来的伦理。”主体性”此时仍是若隐若现,因此,它虽然在君子的个体上表现出来,但它仍然只是社会性的身体之意义,缺乏“主体性”的真实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之前,德尚未完全证得其自身的纯粹性与自足性,“慎独德”始终笼罩在“齐天永命”的心态底下。另外,自孔子开始,人与禽兽之别的话语开始见于不同的文献,先秦诸子不约而同地“将禽兽视为快哉人之为人”的强者之痛,人禽之别话语的出现标志着人之“类意识的自觉”、做人意识的自觉。”人之“天德”“良贵”说将人之“贵”由世间有差等性的社会地位提升至人人皆具的超越性身份,不仅构成了大皆可成圣的人性论的超越根据,也成为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精神资源,谭嗣同(1865—1898)“仁以道为第一义”“道之象为平等”这一近代“仁说”未尝不可被视为是对这一精神资源的重新启动。
孔子不仅强调“有教无类”的普遍人性意识,更明确提出了“修己以敬”的主张,这是一种整体生命的省思意识、一种反思性的处己态度、一种彻底的自我负责的态度(“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毫无疑问,它反映了对自我德性生命的高度专注。“敬”之一字更刻画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关注方式,与“修身西学”中的“关心自我”、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谓的“自我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孔子还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一反身修德的自反性的人生态度,奠定了儒家“君子必自反”的修身路径。“君子”则是先秦儒学修身的目标。观《论语》开篇《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卒篇《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成就君子的人格始终是孔子认定的修身目标。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三十篇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君子”的有八十六章,出现频率最高词是“仁”(109次),其次是“君子”(107次)。修身的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仁之精神”的植根与培养,修身活动源自内在精神的显豁与觉醒,即“为仁由己”之“己”的自立、自决与自强;二是“血气”之对治。早在孔子之前,对治血气就成为君子修身的自觉要求,《国语·周语中》就载有周定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一语。孔子讲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显然,在夫子看来,君子的修身活动应根据血气状态而调整对治的重点。“道(导)血气”(《管子·中篇》)、“平争心”(《左传·昭公十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涵喜怒”(《韩非·竹简·语丛一》:“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庄。”),皆属于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三是言行举止的修饰。《尚书·洪范》已有“敬用”五事的古训,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貌恭、言从、视明、听聪、思睿。《国语·周语》单襄公更是明确指出:“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奔其德,音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君子之“视听言动”关乎国之存亡,可不慎乎!孔子“四勿”之诫(非礼勿视、听、言、动)实渊源有自。《礼记·哀公问》载哀公问孔子何谓“敬身”,孔子答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周易·系辞上》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在《论语·泰伯》中,曾子将君子之道归结为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而在子夏“君子三变”之说中,“望之俨然”即是“动容貌”,“即之也温”即是“正颜色”,“听其言也厉”即是“出辞气”(《论语·子张》)由此亦不难窥见孔子君子人格教育之重点所在。《论语·阳货》载孔子以“恭、宽、信、敏、惠”五者教子张,五种品德显然均是待人接物的德性。对于颜回“何以为身”之问,孔子则回答说:“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数而比于疏,不亦远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虑不先定,临事而谋,不亦晚乎?”(《孔子家语·贤君》,《说苑·敬慎》)“恭”“敬”“忠”“信”既是内在的德性,是“修其中”的对象,又是展现于人我之间的德行。孔子与门人还屡有“君子之道四焉”的说法:“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强于行义,弱于受谏,休于待禄,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六本》)这一类“君子之道四焉”的说法也都是围绕处己、待人、接物展开的。《论语·述而》所记孔子教学的内容为“文、行、忠、信”:文,先王遗文;行,德行;忠,尽力做本分之事;信,诚信待人。这均不外乎君子德行之培育。而所谓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亦均着眼于实际行政能力的培育。诚如狄百瑞指出:君子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志在“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当然儒学是为己之学,健全的人格最终都可归结为“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无疑,“仁之精神的植根与培养”属于“心”的范畴,血气对治属于“气”的范畴,容色与言行举止属于“形”的范畴,心—气—形是由内而外、由隐而显、由心而身的动态结构,此一修身结构在《论语》中已昭然矣。
实际上“士”之本义即“事”,观《尚书》《诗经》《礼记》《荀子》等典籍中“多士”“庶士”“卿士”一类术语,“士”均与“事”联系在一起,士即是在政府部门中担任某种“职事”的人。故“士”又通“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士阶层即是通过学习政治、军事、礼仪的能力而获得从政、出仕的群体。不过,春秋之前的士受到“三重身份”的限定:就社会身份言,士被限定在封建贵族层(当然是最低的一层);就政治身份言,士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上面;而就思想层面言,士则被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士的这三种限定也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不能真正超越自己的身份而形成对现实世界全盘的反思能力。士在春秋时代成为“游士”,丧失了原来“有限的”身份,却也因此形成了“无限的”视野,“处士横议”“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不在其位而议其政”成了一时之“士风”。儒家的伟大之处在于,自孔子始,就给这个新出现的“士”阶层注入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并对士阶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士绝不能为仕而仕,“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士之仕是有原则与底线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秦伯》)余英时指出,先秦的修身观念与士之出处辞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士代表的“道”跟西方教士代表的“上帝”都是不可见的至高权威,唯有上帝的权威由一套教会制度得以体现,而“道”的权威自始就“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士唯有守住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尊、自重,才能显示出其所抱之道的庄严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才能与王侯之“势”分庭抗礼。这是先秦诸子重视治气养心之修身之道的原因所在。……

